良一曲《老石碾》,多少次把我送回我的故乡老屋塆。故乡老屋塆有副老石碾,那老石碾上,正仿佛歌曲中的唱词,它深深的镌刻着我的童年记忆。

我清楚地记得,老屋塆的东边有块大坪,大坪正中躺着一副石碾。只要是大晴大晒的日子,东方还没透亮,那大坪上就会有咿咿呀呀、哐嘡哐嘡的声音,一阵一阵传际。这声音,像一曲西洋敲打乐,有章有法,有点有节,听得人舒服,听得人快畅。这是老屋塆石碾早早地醒了,在为人们劳作而发出的劳动。
从儿时起一直到成年后,我每每过老屋塆的石碾,总免不了要呆呆的审视一会儿——它的规模如此宏大,它的构造如此复杂,我的先人啊,数百年前的举创,着实让后人、感叹。没有起重机起吊,没有车辆运输,安装这样一副石碾,那个日子是怎样的啊?一定是汗水和着辛酸、饥饿伴着伤痛,披星戴月,风餐露宿,凭着两只粗手,一双硬肩,让血躯和聪明智慧撞击出一道道思想火花,才凝聚成这占地面积八十余平方米的石质工程。
我不知道石碾在这里躺了多少年,只知道这一筒一筒围成巨大碾盘的石槽,已磨得光滑如镜,就连碾槽上方的平断面,也磨得不见当年匠人的錾子痕迹,那是朝朝代代塆里的人们有事无事来碾坐,这朝朝代代的居然把碾磨平了。用心想一想,这碾盘是石头啊,石头被人体坐平了,这石碾经历了多少朝多少代呢?

我曾经于小学课本上读到一篇课文《毛在花山》,写的是毛帮当地推碾砣碾麦子的故事,文中还配了彩色插图。仔细看了毛推的石碾,与我老屋塆的石碾大不相同。老师解释说,那是东北的石碾,碾砣像石磙,碾盘像晒羌,碾盘支撑在一个高高的墩子上,人用腰板推石磙,石磙滚动碾麦子。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石磨,原来石碾也是样式众多、千奇百怪啊。
老屋塆的石碾与东北的不同,它安装在露天的大坪上,弯弯的石槽一筒接一筒,连成一个大圆盘,圆盘直径两丈有余,这就是碾盘;两副圆圆的碾砣,如土轮车的轮子大小,一副底面宽,碾米;一副底面窄,碾糠。碾砣中间都穿有木轴心;还有一副木料做的碾架,长有一丈多,形状有如“Y”字,“Y”的两个叉叉的顶端分别装上两只碾砣,“Y”的下面一端有圆圆的榫眼,穿入碾盘中心的固定木轴上。女人坐在碾架上扬鞭吆喝,耕牛拉着碾架悠悠漫步……此情此景,俨然一幅乡村悠闲画卷图。

石碾是把谷子加工成米的器械。然而,那个年代,老屋塆的农户很少有一次装满碾槽的谷子,大多数是碾喂猪的秕糠。小时候的我,没有少上碾盘,那自然是为家里碾猪糠。每次上碾盘,母亲总是头上搭着白底蓝条的格子手绢,胁下夹着箩筐,忙进忙出——等会儿把过了米筛的秕糠拿进屋里把火炒,等会儿把炒熟了的秕糠拿来倒进碾槽里,等会儿蹲在碾盘边筛那已经碾过头遍的秕糠。我坐在碾架上,挥鞭呵牛。绕周旋转的圆周运动,碾盘咿咿呀呀的演唱声,宛若儿时母亲催孩子入眠的曲,让人睡意绵绵,一双眼睛本想尽力睁开着,但仍然抵挡不住睡瞌虫的袭击,不知不觉中那双眼睛又眯着了,时不时招来母亲大声地嚷嚷:不能睏着了,醒醒,醒醒,掉到碾槽里就不得了啦……
半天下来,秕糠终于碾完了。碾停了,牛解了驾,母亲还要忙上好大一阵子。牵牛喝水,驮稻草犒劳牛,卸碾架,退出碾砣轴心,粉糠……一切打理停当,母亲伸起腰背,摘下头上的手绢,连吹带打,将身上的糠灰拍扫得干干净净,然后,看看箩筐里的果实,瞧瞧劳累了半天的石碾,会心地笑了。

石碾是一部读不完的历史。老屋塆的石碾可以说是历史风云的人。我三爹的房子就在村东石碾旁边,大门正对着碾盘,他的肚子里装了不少的石碾的故事。
1946年秋,时任新四军旅旅长的张体学,突出军队重重包围后,率部从罗田北部的安徽金寨出发,经平湖横穿至英山,途中经过北丰河长塘坳。部队翻过项家畈到达我老屋塆时,时间已是大半夜,部队有位级别较高的(一说是张体学)带领部分战士进入老屋塆寻求住宿,一行二十几人在塆中大堂屋过夜,还有近三十名战士睡在村东碾盘上。有战士说,碾盘地势较高,有碾盘石抵挡,可防止蛇虫惊扰。老石碾啊,是你让南征北战的战士们安安稳稳地睡上了一觉,想不到你还为民族的解放,国家的,尽了绵薄之力。
史无前例的“”年代,在“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影响下,老屋塆石碾旁也发生过一幕可笑的事例。
那是1958年初夏的一天晚上,一名驻队住点的领导召开队委会会议,说根据透露的消息,美国和日本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肥料,形状像沙粒,颜色如雪白,说是叫化肥。肥效惊人,拿到田里一撒,不几天秧苗肥绿嫩漾。大家想一想,这种化肥是什么东西做的?那时队里的干部大多是文盲,没见过世面,大家七嘴八舌说不出个名堂来。最后那位驻队领导神秘兮兮地说,都是蠢才,明天看我的。
第二天,就在老屋塆村东的石碾旁,那位驻队领导指挥生产队里干部抬来八口大缸,又派人到李家楼铁厂拿来八口大铁锅。接着又点了十多个青壮劳力,每人一担马桶,让他们把本生产队各塆厕所的大粪挑来,倒入那八口大缸。驻队领导这才津津乐道地宣布:大家考虑到没有,最有肥效的肥料是大粪,美国和日本那种化肥,肯定是提起了大粪的精华部分制作的,怎样的提?不外乎用火熬。于是,围绕老石碾一周,架起了八口大海锅,锅下燃起了熊熊大火,锅里大粪熬得要干时,又从缸里往锅里舀。从下午熬到晚上,大粪熬完了,锅里留下的是一锅稠稠的粪渣。最后的——熬化肥的当场臭倒三人,老屋塆全塆臭得纷纷外逃,家家都是铜锁看门……石碾也是一身,但它不语,默默地承受着。就这样,石碾和老屋塆的村民们一起度过了贫穷,一起了历史的变迁。

石碾作为古老农耕文化的一个缩影,如今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,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老屋塆的石碾同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再后来,竟不见了踪影,那块石碾生息数百年的大坪,竖起了一栋栋楼房。我曾回到老屋塆问我的族人,石碾呢,石碾到哪儿去了。答曰,石碾做了塘岸……
啊,我的老石碾,你真的老了,老得没用了,老了的东西就该遭到如此的命运么?儿时的欢乐,童真的记忆,只有留在那萦萦的梦幻中了。此时此刻,那首《老石碾》的歌曲,又回荡在我的耳畔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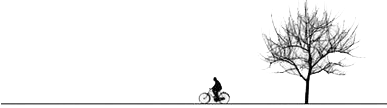
汪习清,男,网名习习清风,亦或清风习习。罗田公共写作研究会副会长,大别山网原创作品版版主。从事教育工作,业余喜好写作,新闻作品散见于《》、《湖北日报》、《黄冈日报》等报刊;教育论文发表于《小学德育》、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》、《班主任之友》等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教育期刊40余篇;文学作品有散文、小说、曲艺、故事近200篇发表于网络及省、市、县文学载体和文学期刊。在各级文学写作大赛中,有15篇散文分别获得二等、三等或优秀;连续三届获得县文化局、文化馆《罗田文艺》编辑部设立的“王葆心文学”。
推荐: